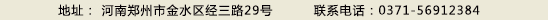妈妈饭
还记得我们当年的最美几代助教吗?本期特邀嘉宾清华数学系毕业生林逸凡给我们讲讲她关于《妈妈饭》最生动、有(dou)趣(bi)的记忆!精彩内容不容错过哦~
都说小时候吃饭是隔锅香,后来年纪越大走得越远,越是想念妈妈饭,因是打小吃惯的家乡味儿,家常味儿。学生时代有一次寝聊聊到这个话题,忽闻R姑娘幽幽说道:我妈妈就不会做饭。有一次她煲田鸡汤,却没切掉田鸡头,我一上饭桌,就看到碧清的汤盆里几只扒了皮的田鸡,像鳄鱼一样浮出来看着我。R姑娘一向善于暗黑系描述,这碗惊悚的田鸡汤把一个晚上酝酿起的脉脉温情冲刷得荡然无存。我的妈妈一向自诩具备先进理念的职业妇女。作为一名讲求实效的人民教师,从准备到上桌超过“一节课”的菜是坚决不做的;作为一名注重养生的微胖界资深美女,杜绝一切辛辣刺激油腻的非健康食品。因此,家里的菜一直是以A炒B加C的形式进行着C_n^k的循环,调味品只三样:酱油,黄酒,盐。是滴,连糖都没有。常做的也就是清炒油麦菜,清炒茼蒿,清炒苋菜,荠菜炒豆腐,茭白炒肉丝,青椒炒银鱼,丝瓜炒毛豆,梅菜炒鸡蛋,笋干炒冬瓜。菜从不多买,每天现买现吃,做的也少,决不剩饭,因此冰箱里经常空空如也,像非洲难民的胃。吃人嘴短,我不敢对此有丝毫怨言。有一次吃清炒红苕尖,母亲忆苦思甜,感慨良多,夹一筷子菜到我碗里劝曰:多吃点,这是你娘我小时候经常挖去喂猪的。母亲大人也不赞成吃零食,像果冻,虾条,薯片,果奶这些垃圾食品,是不能买的。幼儿园组织春游时,给我准备的便当是一个苹果,说是“安全绿色,又顶吃又顶喝”。在那个没有暴漫的年代,我想不出合适的表情回应她。仅有的一次,妈妈做过一道稍微复杂一点的菜,就是把胖茄子的肚子破开,里面填进用蔬菜肉末拌好的馅儿。这个据她说是小时候看外婆做过的,现在忽然想起来做着吃,也算是吃一个念想,吃一种情怀。江浙一带的人似乎特别喜欢把猪肉末填进各种东西里,比如填进青椒里,就是“79卡妞”,填进面筋里,就是“米几卡妞”,我有一次还在同学家吃过“提楼卡妞”,觉得找对象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给我剁田螺屁股。后来对象有了,田螺又在哪里呢,不由一阵感伤。吃着这样的妈妈饭长大,虽没有像李逵老师那样嘴里“淡出鸟来”,却也严重拉低了我对食物的审美。按S姑娘的话说,阿凡的“好吃”一点信息量都没有。相对严苛的饮食条件养成了我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胃口。小时看西游记,对各种妖怪吃食颇感兴趣,知道人家蝎子精请三藏吃的豆沙馅儿和人肉馅儿包子;读红楼梦,见小小丫头对娇红芳香的胭脂鹅脯挑肥拣瘦,我痛心疾首:放开那鹅!让我来!你问我如何把四大名著无缝连接?随至小亭,已设樽俎,盘置青梅,一樽煮酒。“客官歇了脚去,本家有好酒好肉,要点心时,好大馒头!”“不问多少,只顾烫来,也把二三十个馒头来下酒。”于是将那人油炒炼,人油煎熬,熬得黑糊充作面筋样子,剜的人脑切作豆腐块片,两盘端到面前,道:“长老慢用,后面还有添换来也。”长老探头一闻,皱眉道:“这油腻腻的,谁吃这个!”八岁那年,我终于把母亲惹毛了。在她的大学同学聚会上,我把每样菜都尝了个遍,最后用一小块馒头,把盛炼乳的碟子擦的干干净净。在妈妈主持下的除夕夜年夜饭,依旧是不变的C_n^k,顶多把系数n调大一点而已。开心果腰果啥的也蹭上来充两个冷盘,再到外面买点猪舌头烧鸡啥的,就齐活儿了,主张环保提倡文明,鞭炮也从来不放的,年味儿淡薄得要起高原反应。好在山谷里的野百合也有春天,寡淡的年夜饭之后,就是去外婆家啦。外婆家在农村,像每个上了年纪的长辈一样,外婆是照例要嫌我瘦的。三岁的时候曾经在外婆家寄养了半年,这半年里,被外婆充满慈爱的手做出的芝麻花生糖和梅菜猪油渣酥饼喂成了一只胖乎乎的皮球。刚去的时候害怕地上的鸡屎,哭着天天要人抱着不肯下地,六个月后爸爸妈妈来看我,看到一个肉嘟嘟的背影,正蹲在地上用一根树枝挑了地上的鸡屎来玩。妈妈一看发展不妙赶紧把我又接了回去。长大了去外婆家,也只有过年才去了。外婆做的一手好饭,小有名气,碰上村里有人赶事,常常被人请去帮厨掌勺。外婆做的菜有着一股清新自然的山乡风味。相比城镇,外婆有着得天独厚的食材条件。米是自种自磨的,三楼放着一架很大的鼓风机,上面用毛笔写着“去伪存真”四个大字,已经被岁月侵蚀得有些斑驳了。外婆做的饭是正宗的柴火饭,有着沉甸甸质感的木头锅盖,嵌在灶里的厚重铁饭锅,用来烧火的是山上枯枝落叶。煮出的米饭香喷喷,更有锅底的一层香脆的锅巴,撒上一点点盐就很好吃了。我最喜欢烧火,坐在灶台后面,一把一把地往里添柴,火光照着人脸红扑扑,没多久整个人都暖和起来。有时放几个芋头或者山药进去烤着,香极了。旁边的柴火堆是母鸡们下蛋喜欢去的地方,常常能摸到几个还热乎着的鸡蛋,也是小小的惊喜。外婆家的糯米粉也是自己磨的,手工捏制的年糕又软又弹牙,口感跟机器压的完全不是一回事,真真好吃极了。用来做芹菜猪肉馅儿的大汤圆也相当不错,那汤圆鸡蛋大小,不是浑圆的,而是像酷儿一样,头顶长出一个尖儿。糯米类的东西是很“扛硬”的,这么大的汤圆小时候的我一次能吃八个,水平跟舅舅和姨夫相当。每年过年,村里家家户户都要用竹竿挂出自家灌的香肠,虽然材料做法都一样,可家家的味道还是各有不同,香肠做的好不好吃,也是考量这家媳妇能不能干的一个方面吧,我瞎猜的,嘻嘻。还有大肥鸭子,自家养的鸭,提前杀好了也给拔了毛挂在竹竿上风干,吃的时候放进瓦罐,加入冬笋用小火慢慢煨,直到鸭肉酥烂,笋的鲜味与鸭肉的鲜味融为一体,散出阵阵诱人的芳香。我向来是不爱吃鸡鸭肉的,可是外婆家的这道烧鸭子确实非吃不可。有时初一白天到了外婆家,看见竹竿上的鸭子毛没有完全拔干净,就偷出妈妈的眉毛镊子,给它做最后一次全面而细致的美容。等到晚上鸭子端上桌,叆叇蒸腾的水汽中,有一种宗教般虔诚的感召气氛,要引出吃货激动的泪水来的。外婆做的萝卜丝饼也特别好吃,外酥里嫩。浇一勺烫面进模子下油锅炸定型,在酿进萝卜丝豆腐猪肉末,然后再上面在浇一层烫面盖上。饼子要现炸现吃才最好吃,巴巴守在锅边,也不顾烫嘴,接过张口就咬。外面的酥皮“咔嚓”一声咬碎,鲜美的油汁子就顺着嘴角流下来。脑海里也咕嘟咕嘟泛起幸福的油花!相同的馅料还可以做豆腐皮包子,用薄薄的油豆皮裹上馅儿做成春卷样子的细长卷儿下油锅一炸,也是过年常吃的一道家常美味。此外我爱吃的还有烟熏老豆腐,荞面猫耳朵,荠菜馄饨,梅菜扣肉,面筋嵌肉,都平平常常的菜,但因着食材的新鲜和野意儿,哪怕一棵地里的油菜,一尾山溪里的小鱼,经过外婆那一双勤劳的慈爱的巧手,也能做出异乎寻常的好味道。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外婆家乡过年人人都要吃的一道特色菜:六笋捂肉夹馒头。小时候觉得它味道怪,馒头对我来说又太大,不大爱吃,后来长大了,在外背井离乡,却常常莫名的想念那个熟悉的味道。对我来说,一吃到六笋捂肉夹馒头,就像是过年了。后来自不量力想要自己动手做着试试看,一问之下大吃一惊,看着简简单单的一道菜做起来居然要这么费事。首先要摘上好的六笋晒成干,泡发后片成纸那样薄,然后用水煮沸,再用木锤子捣,既不能太老也不能捣太烂,然后再把事先腌制半个多月的猪头肉用开水煮烂,片成薄片下油锅炸至金黄,肉汤里放进捣好的六笋一起炖烂。夹六笋和猪头肉的馒头不知道怎么做的,特别的虚,像发糕,形状浅浅大大的,像个小碟子,吃的时候就把这个馒头碟捧在手里,夹一点六笋,上面盖几片肉,就可以趁热吃了。六笋的味道很特别,如果不是从小吃,很可能不惯那个味道,也品不出好坏。这个菜很考验功夫,家家户户做出来的味道也是各有不同的,我就只想吃外婆做的那个味道,因此别说外地没有,就是外地有卖,跟杭州小笼包一样遍地开花,也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味儿了。如今的我长大了,早已过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年纪,吃食堂,下馆子,在各种地方口味间颠沛流离,随遇而安地度过了学生时代。后来,终于有自己的厨房了,也就有了“今天晚上吃啥”的话语权。初到东北,住在辽源老齐租来的小小屋子里,我挥舞着锅铲,像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小勇士,誓要在这一片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的土地上杀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第一次做的成品上桌,有开始打算做酸辣后来改醋溜结果啥也不是的土豆不成丝,有外焦里生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糖醋排骨,还有我大言不惭称其为“饭后甜点”却被老齐毫不留情嘲笑的“炸面饼子”。这顿饭以摩拳擦掌开始,以垂头丧气结束。
后来的后来,做饭的技术慢慢地有了些进步了,油炸虾,红烧肉,炖猪蹄,煎鳕鱼,兴致勃勃地玩儿了一圈下来。然而鱼生火,肉生痰,我的口味也开始出现返祖,慢慢的开始想念外婆乡野气息的农家美味。然而外婆家的饭菜毕竟只是特别的日子里才吃的,是过年的记忆,后来的后来的后来,最最怀念的竟然还是妈妈那些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清汤小菜。可是上哪里去找那些茭白荠菜马兰头呢?哪怕是最简单的油麦菜,也狐疑总是炒的不如妈妈的好啊,饭也不如妈妈煮的香。妈妈不善于做面食,却是让我吃惯了。疙瘩汤里的疙瘩?要做的大大硬硬的才好吃,摊鸡蛋饼?要厚厚的才有嚼劲。
后来妈妈来东北看我,老齐说,我觉得妈妈炒的油菜和你的差不多啊。我瞪着眼看着他,慢慢明白自己没心没肺了二十多年,确实到了思念妈妈饭的年纪了。
璇玑(xuanzhang)转载请注明:http://www.cnmaozhan.com/ymcxg/96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