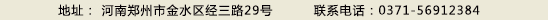围炉黑土麦田一方水土有清音
湘西地界群山蜿蜒连绵,远望是青色,近看有缀缀金黄——是南太的大米来到了秋天。清水江一脉流去,隔开的是湖南和贵州,站在山头,遥遥相望。磨老村就藏在这山水幽径间。在张雪婷的头脑画卷中,每天早上,这条江都氤氲着虚渺的雾气,缭绕在山头林丛,仿坠仙尘。冬季却同西南多数山寨一样弥漫着阴冷的湿气,春季乍暖还寒,总觉夏天的步伐迟迟未来。村落周遭杂种着许多四季草木,雪婷多数叫不出名字,但她常和伙伴从村子沿河往镇上去,路边采野花追晚霞,没有名字的河塘清澈,奶奶和黄牛都对着她笑。
南太大米
湘西奶奶和耕牛
磨老村是一个传统苗族村落。与国内多数乡村一样,村民们谨循着朝耕暮休的作息。农闲时在河滩上放牧水牛,忙时则稼穑农事,大体看上去自在方便。村民通常一日二餐,早早起床,九点左右吃早饭,一直耕忙到下午5、6点才吃晚饭。遇上红事白事,全村的村民都会一起帮忙,吃流水席[1]等。白事晚上通常会做连续2-3天的法事,村子里其他重要的事会请巴代师傅[2]来帮忙。
对张雪婷来说,自小在北方农村成长的她对磨老村最深刻的印象便是南北农村的差异。在她的幼年印象中,北方农村往往都是大片连成的土地,而她小时候常见到的手工耕种方式如今也已被机器取代。但在这个南方村落,水牛耕田、村民插秧等传统耕种方式仍然四处布罗着,张也时常看到家家户户养鸡养鸭,村子里的老爷爷,还会常常上坡放牛,老奶奶,还会低头苗绣。而传统的苗鼓苗歌,亦常常悠扬飘荡在山河之间,天地旷大,一如亘古。
磨老村建筑
关于磨老村的来历,雪婷也略有耳闻。花垣县的另一个镇子吉卫里有一个龙姓子弟,他救了一位黄将军,作为回报,黄将军让他们自己选择了一片土地予以赠送,他们选择了一片深山老林,也就是现在的磨老村。从那以后,原来居住在这路的潮汕人往后退了五公里,都定居这里,称木老(深山老林之意),往后逐渐演变为磨老这个名字。
去年(年)有一项脱贫致富的工作落实到磨老村。按照脱贫的指标,人均年收入达到元则被视为脱贫。而去年的脱贫被称为“精准扶贫”,其所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扶持产业发展实现从输血到造血,以及建立合作社、土地确权等对农村的生产关系等。对磨老村来说,这些已是相当大的改变。
村子里的老人和妇女对生活之不易更加感受深重。他们每日耕种劳碌,加上磨老村因为土地被一条河隔着,近几年没了船,很多田土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到达,这些无疑都是农村生活的细琐艰难。
然而一些村民的生活仍然辛苦,生老病死四字,对他们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生病,对于富裕的城里人来说可能只是一场手术,几月住院,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从村中优越人家直接掉落贫困线以下的劫难。大病返贫,是这个小村子里讳言的不幸。龙衡山的两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本是村里人人羡慕的一家,去年孙女大病一场,新农合[3]不覆蓋的毛病,连县里的卫生院都住不起,更从何谈医院?
外出打工的人则更看重打工给一个家庭带来的改变。然而,在那些大病返贫的家庭里,中年人在外打工寄回来微薄的收入,全用在看病上了。最不幸的却是家里顶梁柱的倒下,村里留守的大都是孩子和老人,生活基本靠着中年人在外打工的收入支持。此时这个主要收入来源若断了,对整个家庭的打击无疑是毁灭性的。
而很多时候,能干的人也能培养出更优秀的下一代。例如,一个家庭的儿子在张家界读大学,特种专业,出来工作包分配,龙一明夫妇在村子里无比光荣。而他们夫妇俩本身也是村子里最能干的一对。两排砖房,一边酿酒,一边养猪,酒糟可以喂猪,这在设备落后的农村是先进的利用观念。作为村里的富裕户,他们家也造起了楼房。
水桶村的猪
陈旖雪的身后跟着一只念念不忘的狗。旖雪第一次进水桶村走访的时候,进一个大叔家。大家都老实,站着坐着,等人开口。旖雪见地下有个大南瓜,当搭讪着问这个南瓜怎么吃。大叔说,喂猪。结果走的时候,大叔非要把这个南瓜送给她。推辞不下,收了。回到村委会,一看房里堆了好多南瓜——村子里的人都以为她爱吃南瓜,全给送来了。湘西水桶村对于这个从小在天津吃着包子长大的女生来说,和沈从文的笔下有很大不同。《边城》的故事发生在民国,而这时代感,到如今已大不相同。但“在这条长河里,他们总能去适应,去生活”,旖雪对农村有了一些更理解、更包容的认识。之前对乡村的认知是来自书本文献,那是别人的村庄。到底和自己的村子不一样。开口说道:“我的村子……”无关主权,而是牵挂、责任和明天。书本上被固化的东西,变成真实的案例,改变了旖雪长久以来的认知。对性别的白癜风患者的饮食安徽治疗白癜风的医院
转载请注明:http://www.cnmaozhan.com/ymccp/94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