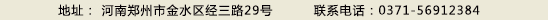关于饮食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吃货变成了一种正向标签,成为热爱生活的代名词。可是注定美食吃货少,被动吃货多,什么都想尝一尝,吃完拍拍肚子说要减肥——下顿饭之前。可是,如果连吃都不能满足的话,那中青年人的生活也未免太苦了。
说到吃,任谁都可以连说好几天,所以我决定把我想到的写下来,尽可能写得完备,之后就知道哪些是我早已了解的,哪些又是我新发现的。
对吃的记忆,大致来源于三个地方,一个是陕西,然后是广东,最后是江浙沪,遇到不同的人和食物,会了解不同地区的差异和特点。
北面南米,北方多主食,尤其西北,面食总是排第一。我印象里的西安美食,凉皮肉夹馍,泡馍葫芦头,油泼面裤带面,都是主食,肉夹馍再好吃也不会有人吃两个。被归为小吃的几种也是一份分两份,量变小而已。一般陕西的餐馆都会使用巨大的碗盘,倒不是模仿西餐餐桌文化,而是碗盘够大才装得下正常分量的饭菜。至于菜式,我也没听过称得上特点的陕西菜,即使有十大菜系,也不会包含陕菜。陕南靠近四川重庆,陕北则像山西宁夏的聚合体,关中的饮食特点有一半都是回族同胞带来的,剩下的部分在面粉上做文章。在别人看来不就是一碗面嘛,在陕西人看来那可是天大的事。《白鹿原》电视剧有白嘉轩吃新儿媳做的油泼面一段,小说里没有,但电视剧有,视觉影像有必要,也贴合实际,这一碗油泼面获得了一个老庄稼人的肯定,在这个新家里算是地位确立了,之后大概还要再和新妈妈再切磋一阵。
至于广东,则是在原有味觉基础上,吸收了长三角以及众多南方省份还有国外的饮食特点,兼容并包,加上本味基础雄厚,经济发达,因此无论在庙堂还是在街角,都极具特色。
在这里,广州主要体现兼容并包,潮汕雷州体现本味,这一点我倾向于认为,人口流动和经济发展作用明显。粤菜是四大菜系之一,比较有名的有椒盐濑尿虾,烤乳猪,阿一鲍鱼,姜葱焗肉蟹,护国菜……,这些我都没吃过。但是这不影响我流口水、写心得。我吃过的有白切鸡,叉烧,虾饺,蟹黄包,肠粉,河粉,炒粉,牛杂,云吞,濑尿虾,卤水拼盘,牛肉丸,酿豆腐,梅菜扣肉,早茶,靓汤,腌面,煲仔饭,鱼头豆腐,咕咾肉,萝卜牛腩,潮汕火锅,这个粥那个粥,这个鱼那个鱼,这个虾那个虾……,还有变了味的青岛啤酒。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都可以找到满足自己口舌的美味。
粤菜有一道“咕咾肉”比较有意思,后来知道两广是菠萝主产区。这种搭配的妙处在于,菠萝蛋白酶有水解蛋白质的功能,起到了嫩肉的作用。发明这道菜的厨师可能不知道原理,但是这种搭配呈现的效果足够引起人的食欲。另外,菠萝卖的时候用盐水浸泡,也是为了分解菠萝蛋白酶,降低口腔的刺痛感。
还有一道豆豉鲮鱼油麦菜,开始我很好奇,平凡如油麦菜,竟用豆豉加鲮鱼来配,而且价格实惠,直到在厨房里看到了一种豆豉鲮鱼罐头。
最有特点还是要说早茶,这大概是唯一让人愿意周末早起的事情了,各种点心、菜式可以一直吃到中午,另外,早茶是休闲的活动,也是中国的酒桌文化另一种形式,而且因为并不会胡吃海喝,反而是一种更理想的生意场(一早起床精神抖擞去“谈生意”,比凌晨像一只湿垃圾桶回家体面多了)。
最后是江浙沪。在上海开埠之前,江浙是中国最富饶的地区,江南省分治导致的争吵遗留至今,合肥难肥,南京顶着徽京的帽子在省内不受待见,可是苏州也永远取代不了南京的地位,中国最重要的三个古代帝都城市里,南京自有其重要性。南京也是我除西安之外见到的最具历史感的城市,江宁织造府,两江总督府,太平天国伪皇宫,民国总统府竟然在同一处位置。改名中华门的聚宝门,结构、工艺之高超,令人叹服。相比于西安,是鲜活的历史城市。
至于美食,苏菜,浙菜,淮扬菜,还有后起之秀本帮菜,组成了庞大的美食阵营。太湖粮仓,阳澄湖大闸蟹,舟山海鲜,金华火腿,杭州龙井,嘉兴五芳斋,绍兴黄酒,宁波青团,不一而足。长江横向来带长江流域物产和京杭大运河竖向的沟通,让这片区域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只是一个缩影,一个展现江浙地区特征的名片。杨广年轻时也意气风发,最后却沉迷在扬州声色里感叹“好头颈,谁当斫之!”,最终做了去礼远众的隋炀帝。
对于美食,和其他事物一样,同样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平凡而伟大。像小时候的味道,永远留在心底,嗅到了别人家飘出窗外的饭菜味,也会为之感动,即使只是普通炒饭。有一个著名的典故,晋代名仕张翰以想念家乡莼菜、鲈鱼为由,远离政治。后来辛弃疾调侃“休说鲈鱼堪脍”,可辛弃疾也是在时运不济,命途多舛的情形下嘴硬而已。有多少人在人生失意的时候不会有自己的莼鲈之思呢?
另一个是可遇不可求。千金难买双头鲍,吃在嘴里的除了食物本身的味道,还有一种尽享天物的虚荣。“黄芩无假,阿魏无真”,原本珍贵的的东西,也入得了普通人之口,说明珍贵已不如原本的珍贵,不能赶上食客需求的物种,便只能无奈的走向灭绝。张爱玲说人生有三恨,一恨海棠无香,二恨鲥鱼多刺,三恨红楼梦未完。鲥鱼的鲜美我不知道,但是可以查到的是,距离灭绝也不远了。谁让你生的好,进化的速度却又赶不上人类的需求。
关于口味。
天津的狗不理,阳澄湖大闸蟹,清江鱼,武昌鱼,武汉热干面,汉中热米皮,常熟叫花鸡,镇江锅盖面,苏州的莼鲈,宁波的咸齑和黄鱼,浙江的梅干菜,新疆的馕饼,甘肃的锅盔,渝蓉的青椒……,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饮食特征,这种长期对一种口味的认知,发展成为对一类食物口味的追求,这种追求,往往是和当地主产物以及气候联系起来的,比如东南方多鱼米,西北方多面牛羊,四川重辣重麻。也只有日复一日对这种口味的理解,发展成为一种对最细微的变化的敏感。因此换了地方,食物就是往往变了味道,甚至变成另一种怪异的东西。
在上海的时候,看到有一家面馆竟然有泡馍,结果发现,其实是一种菜汤配饼!后来想想这其实是合理的,街边小店并不能容纳做一份正宗泡馍需要的设备,重油重盐的口味也难以匹配上海人的口味。如果是在西安,等了半天发现端上来是一碗这样的东西,食客可能会大骂一句——你做(zou)的倒是个锤子!
还有一次吃馒头的经历,那是在青岛的一家大食堂,非常普通的一块馒头,甚至还有点凉了,但是相比起来,在其他地方吃到的只能算是面粉团。简单如馒头的食物,在原产地才真正被注入了灵魂。
茨威格写维也纳人对艺术生活的追求。无论上层名流直到皇帝本人,或者是平民,都对艺术或者说戏剧有着近似荒唐的偏爱。这种偏爱,也养成了对艺术无与伦比的鉴赏力——经过长达几个世纪的艺术熏陶。
“维也纳的音乐家和演员们都清楚自己在这座城市中的地位。不论在维也纳歌剧院还是在皇家剧院,来不得半点马虎。任何一个错音都会立刻被发现,一旦进入合声部的时间不合拍或者音符略短,都会立刻受到指责。这种监督不仅来自首演时的专业评论家,也来自现场观众。通过不断的比较,他们的听觉越来越灵敏。”
那么不到原产地就吃不到正宗的东西吗?显然不是。我倾向于认为这取决于食物的特征和所能带来的经济收益。也就可以解释火锅为什么可以全国畅销,馒头到了南方容易变味道。另一点是不同地区的人对食物本就有不同的偏爱,正宗与否并不绝对凌驾于饮食习惯。在美国中餐馆,可能会出现一份炒面配春卷,喝的是一杯百事。在中国人看来这实属怪异,但对于他们,也许会觉得,大概中国人自己也没发现这么棒的吃法。(我们也有十分熟牛排配白米饭的故事)说到最后,永远避不开《红楼梦》,即使吃只是作为一个方面,但描写范围之广,亦足以膜拜,第四十一回写到茄鲞(xiǎng)这道菜,常被拿出来作为案例。原文是这样的:贾母笑道:"你把茄鲞搛些喂他。"凤姐儿听说,依言搛些茄鲞送入刘姥姥口中,因笑道:"你们天天吃茄子,也尝尝我们的茄子弄的可口不可口。"刘姥姥笑道:"别哄我了,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众人笑道:"真是茄子,我们再不哄你。"刘姥姥诧异道:"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这一口细嚼嚼。"凤姐果又搛了些放入口内。刘姥姥细嚼了半日,笑道:"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象是茄子。告诉我是个什么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凤姐儿笑道:"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籤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都切成钉子,拿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他,怪道这个味儿!"关于这一段,知乎上有一个提问“如何评价苹果与陈可辛合作短片《三分钟》?”用户“景晨”把《三分钟》和茄鲞做了比较,IPhone在这里就是那只茄子,陈可辛做出来是“茄鲞”,普通人做出来则是刘姥姥印象里的茄子,比喻恰到好处。
引用问答:如何评价苹果与陈可辛合作短片《三分钟》?
文章:中国的“菠萝的海”在哪里?浙江人的命,都是梅干菜给的!(来源:地道风物)
电影:《饮食男女》、《食神》、《三分钟》、《白鹿原》;
书:《昨日的世界》、《鱼翅与花椒》、《红楼梦》。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转载请注明:http://www.cnmaozhan.com/ymczf/11423.html